

凯发k8娱乐官网app下载随着机器大工业日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科学技术二重性初步认知的基础上,又大量学习了工艺史与科学史的相关著作,并结合科技在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实际效应,对科技的异化效应和生产力促动效应的认识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更为深入,并明确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重要论断,高度肯定了科技的生产力性质。这一认识的深化过程主要体现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党宣言》、《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之中。

首先,在1847年,马克思撰写并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在该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政论家蒲鲁东极其荒谬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的批判,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并通过对分工与机器的进一步考察,再一次肯定了科技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而明确了科技的生产力性质;同时,透过工人在分工与机器宰治下的悲惨境遇,也进一步阐述了科技的异化效应,并指出了科技异化的根源k8凯发。

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对分工与机器的荒谬认知,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物化形态——机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在分工与机器这一章,蒲鲁东认为分工是贫困的源泉,而机器的使用作为多种操作的集合,使被分化的劳动者重新复原,因而构成了分工的否定。马克思通过对分工与机器关系的考察,无情地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分工与机器关系认识的颠倒性、荒谬性。马克思认为机器不仅不是分工的否定,而且构成了分工扩大的必要条件。因为,机器只是各种生产工具的组合,而不是劳动者各种生产活动的组合,同时,分工随着机器的发展而扩大,机械性劳动资料的每一次发展都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机器的革新决定劳动的组织形式与划分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机器的发明与革新推动了产业部门的分化与细化k8凯发,从而扩大了世界市场。机器的发明不仅推动了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分离,也打破了生产的地域界限,形成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诚如马克思所言:“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马克思发现,自1825年以来,一切新机器的发明与技术改进大都是工人的结果。在工人每一次之后,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新机器。在资本与自动机器体系的结合下,对机器进行一切改进的目的都是取消人的劳动。这样一来,工人全部的工作内容仅仅是监督机器的运转,只涉及注意力的使用,因而造成了人的简单化。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代替了工人的部分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工人的职能,“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但是与以往认为分工造的简单化不同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对分工采取了一种更加辩证的态度。他认为在自动的机器体系下,工人摆脱固定不变的工序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可以在监管多台机器的过程中学会多种业务并扩大自身的眼界。可以说,此时马克思对科技异化效应的认识比过去更加深入和科学了。其次,《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根据1847年12月的演讲而完成的一篇短文。在该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工资问题的分析,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来源,并以此深化了对科技的生产力性质与异化效应的认识。

一方面,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扩大和细化了社会分工,并极大地促进了机器的改进与应用。马克思在讨论资本增长对工资的影响问题时,重点分析了科技的生产力性质。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的发展,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所以,资本家只有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而资本家降低生产成本的办法只能是细化社会分工、改进生产方法以及在生产中采用更为先进的机器。
因而,哪个资本家能率先实现生产工序的精细化、率先在生产中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与机器、率先提高工艺水平以及在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效率上实现对自然力的利用,那么,该资本家便能比其竞争者迅速的缩减生产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使其有可能更廉价地卖出商品而没有丝毫损失,从而占据更大的销售市场。

当其他竞争者发现他取胜的奥秘时,他们便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并在更大的规模上使用机器和细化社会分工,所以便加剧了资本家之间关于分工与机器的竞争,并大大刺激了机器的革新与应用。这样一来,分工必然引起进一步分工,机器生产必然进一步促进机器的采用,劳动必然进一步扩大劳动的规模,不允许分工与机器有片刻的停息。所以,分工将会不断细化,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也会不断扩大。正是基于此,使马克思更加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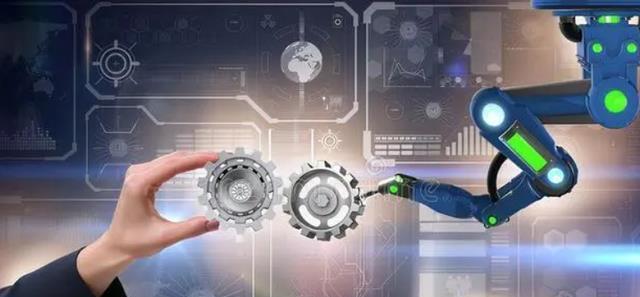
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关于分工与机器的激烈角逐,既加剧了工人身体的耗费和片面化,也使工人日益被淘汰而变得过剩。从分工来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分工不断细化,这样一来,工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局限于某一细小工序,工作内容愈来愈简化,以致具有熟练技能和较高技艺的工人被四面八方的普通竞争者所排挤,竞争越是激烈,工资也就越是降低。如果工人想维持原来的工资水平和缓解生存压力,就必须进行更多的劳动或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生产率,工人越是拼命劳动,工资越是降低,他们就越是贫困,越是恶化自身的处境,以致劳动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令人生厌的力量。

从机器来看,由于机器的不断革新与全面应用,机器体系愈益成熟,工资再度降低,大量的成年工人被童工所取代,成为生产过剩者。在生存的压力下,“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就像森林似的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如果工人不愿意领取极其微薄的工资,那结果便是整个家庭的毁灭;反之,他们只能摇尾乞怜,在这种异己的力量宰治下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强度。总之,分工越是细化,应用机器的规模越是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是残酷,他们的生存处境就越悲惨。

再次,1848年2月,《党宣言》正式出版。在这篇纲领性文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资产阶级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衡量标准,科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这里,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明确使用科技的字眼,但是他们却以机器、大工业、世界市场等概念表达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变革的推动作用,从而以此对科技的生产力性质与异化效应进行了深度考察。
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资产阶级对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性变革为参照,高度肯定了科技的生产力性质。由于蒸汽机的使用催生了工业,大大促进了商业、航海业与水陆交通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伴随着这一发展过程逐步登上历史的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及资产阶级性的历史作用时曾指出:资产阶级打破了一切封建羁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由于这种性的历史作用是通过科技得以实现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正是在生产的不断变革、社会的不安定和变动中,一切生产工具得以迅速改进、交通工具得以不断革新,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由有限的地域性存在发展为全球的脱域性存在,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充满意义的历史作用的阐述,高度赞赏了科技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